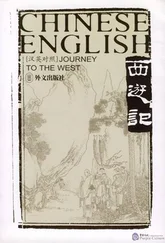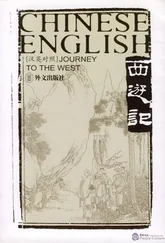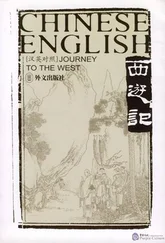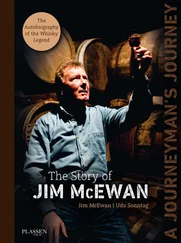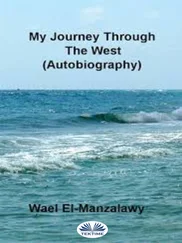詩曰:奉法西來道路賒,秋風漸浙落霜花。乖猿牢鎖繩休解,劣馬勤兜鞭莫加。木母金公原自合,黃婆赤子本無差。咬開鐵彈真消息,般若波羅到彼家。這回書, 蓋言取經之道,不离乎一身務本之道也。卻說他師徒四眾,了悟真如,頓開塵鎖,自跳出性海流沙,渾無挂礙,徑投大路西來。歷遍了青山綠水,看不盡野草閒花。 真個也光陰迅速,又值九秋,但見了些楓葉滿山紅,黃花耐晚風。老蟬吟漸懶,愁蟋思無窮。荷破青褲扇,橙香金彈叢。可怜數行雁,點點遠排空。
正走處,不覺天晚。三藏道:“徒弟,如今天色又晚,卻往那里安歇?”行者道:“師父說話差了,出家人餐風宿水,臥月眠霜,隨處是家。又問那里安歇,何 也?”豬八戒道:“哥啊,你只知道你走路輕省,那里管別人累墜?自過了流沙河,這一向爬山過岭,身挑著重擔,老大難挨也!須是尋個人家,一則化些茶飯,二 則養養精神,才是個道理。”行者道:“呆子,你這般言語,似有報怨之心。還象在高老庄,倚懶不求福的自在,恐不能也。
既是秉正沙門,須是要吃辛受苦,才做得徒弟哩。”八戒道:“哥哥,你看這擔行李多重?”行者道:“兄弟,自從有了你与沙僧,我又不曾挑著,那知多 重?”八戒道:“哥啊,你看看數儿么:四片黃藤蔑,長短八條繩。又要防陰雨,氈包三四層。匾擔還愁滑,兩頭釘上釘。銅鑲鐵打九環杖,篾絲藤纏大斗篷。似這 般許多行李,難為老豬一個逐日家擔著走,偏你跟師父做徒弟,拿我做長工!”行者笑道:“呆子,你和誰說哩?”八戒道:“哥哥,与你說哩。”行者道:“錯和 我說了。老孫只管師父好歹,你与沙僧,專管行李馬匹。但若怠慢了些儿,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!”
八戒道:“哥啊,不要說打,打就是以力欺人。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,你是定不肯挑;但師父騎的馬,那般高大肥盛,只馱著老和尚一個,教他帶几件儿,也是 弟兄之情。”行者道:“你說他是馬哩!他不是凡馬,本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,喚名龍馬三太子。
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,被他父親告了忤逆,身犯天條,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,他在那鷹愁陡澗,久等師父,又幸得菩薩親臨,卻將他退鱗去角,摘了項 下珠,才變做這匹馬,愿馱師父往西天拜佛。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,你莫攀他。”那沙僧聞言道:“哥哥,真個是龍么?”行者道:“是龍。”八戒道: “哥啊,我聞得古人云,龍能噴云曖霧,播土揚沙。有巴山捎岭的手段,有翻江攪海的神通。怎么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?”行者道:“你要他快走,我教他快走個儿 你看。”好大圣,把金箍棒揝一揝,万道彩云生。那馬看見拿棒,恐怕打來,慌得四只蹄疾如飛電,颼的跑將去了。那師父手軟勒不住,盡他劣性,奔上山崖,才大 達辿步走。師父喘息始定,抬頭遠見一簇松陰,內有几間房舍,著實軒昂,但見:門垂翠柏,宅近青山。几株松冉冉,數莖竹斑斑。
篱邊野菊凝霜艷,橋畔幽蘭映水丹。粉泥牆壁,磚砌圍圜。高堂多壯麗,大廈甚清安。牛羊不見無雞犬,想是秋收農事閒。
那師父正按轡徐觀,又見悟空兄弟方到。悟淨道:“師父不曾跌下馬來么?”長老罵道:“悟空這潑猴,他把馬儿惊了,早是我還騎得住哩!”行者陪笑道: “師父莫罵我,都是豬八戒說馬行遲,故此著他快些。”那呆子因赶馬,走急了些儿,喘气噓噓,口里唧唧噥噥的鬧道:“罷了!罷了!見自肚別腰松,擔子沉重, 挑不上來,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赶馬!”長老道:“徒弟啊,你且看那壁廂,有一座庄院,我們卻好借宿去也。”行者聞言,急抬頭舉目而看,果見那半空中慶云籠 罩,瑞靄遮盈,情知定是佛仙點化,他卻不敢泄漏天机,只道:“好!好!好!我們借宿去來。”
長老連忙下馬,見一座門樓,乃是垂蓮象鼻,畫棟雕梁。沙僧歇了擔子,八戒牽了馬匹道:“這個人家,是過當的富實之家。”行者就要進去,三藏道:“不 可,你我出家人,各自避些嫌疑,切莫擅入。且自等他有人出來,以禮求宿,方可。”八戒拴了馬,斜倚牆根之下,三藏坐在石鼓上,行者、沙僧坐在台基邊。久無 人出,行者性急,跳起身入門里看處: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,帘櫳高控。屏門上,挂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;兩邊金漆柱上,貼著一幅大紅紙的春聯,上寫著:絲 飄弱柳平橋晚,雪點香梅小院春。正中間,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几,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。
上有六張交椅,兩山頭挂著四季吊屏。
行者正然偷看處,忽听得后門內有腳步之聲,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,嬌聲問道:“是甚么人,擅入我寡婦之門?”慌得個大圣喏喏連聲道:“小僧是東土 大唐來的,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。一行四眾,路過寶方,天色已晚,特奔老菩薩檀府,告借一宵。”那婦人笑語相迎道:“長老,那三位在那里?請來。” 行者高聲叫道:“師父,請進來耶。”三藏才与八戒、沙僧牽馬挑擔而入,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。八戒餳眼偷看,你道他怎生打扮:
穿一件織金官綠紵絲襖,上罩著淺紅比甲;系一條結彩鵝黃錦繡裙,下映著高底花鞋。時樣鬘髻皂紗漫,相襯著二色盤龍發;
宮樣牙梳朱翠晃,斜簪著兩股赤金釵。云鬢半蒼飛鳳翅,耳環雙墜寶珠排。脂粉不施猶自美,風流還似少年才。
那婦人見了他三眾,更加欣喜,以禮邀入廳房,一一相見禮畢,請各敘坐看茶。那屏風后,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,托著黃金盤、白玉盞,香茶噴暖气,异果 散幽香。那人綽彩袖,春筍纖長;擎玉盞,傳茶上奉。對他們一一拜了。茶畢,又吩咐辦齋。三藏啟手道:“老菩薩,高姓?貴地是甚地名?”婦人道: “此間乃西牛賀洲之地。小婦人娘家姓賈,夫家姓莫。幼年不幸,公姑早亡,与丈夫守承祖業,有家資万貫,良田千頃。夫妻們命里無子,止生了三個女孩儿,前年 大不幸,又喪了丈夫,小婦居孀,今歲服滿。空遺下田產家業,再無個眷族親人,只是我娘女們承領。欲嫁他人,又難舍家業。适承長老下降,想是師徒四眾。小婦 娘女四人,意欲坐山招夫,四位恰好,不知尊意肯否如何。”三藏聞言,推聾妝啞,瞑目宁心,寂然不答。那婦人道:“舍下有水田三百余頃,旱田三百余頃,山場 果木三百余頃;黃水牛有一千余只,況騾馬成群,豬羊無數。東南西北,庄堡草場,共有六七十處。家下有八九年用不著的米谷,十來年穿不著的綾羅;一生有使不 著的金銀,胜強似那錦帳藏春,說甚么金釵兩行。你師徒們若肯回心轉意,招贅在寒家,自自在在,享用榮華,卻不強如往西勞碌?”那三藏也只是如痴如蠢,默默 無言。
那婦人道:“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。故夫比我年大三歲,我今年四十五歲。大女儿名真真,今年二十歲;次女名愛愛,今年十八歲;三小女名怜怜,今 年十六歲,俱不曾許配人家。雖是小婦人丑陋,卻幸小女俱有几分顏色,女工針指,無所不會。因是先夫無子,即把他們當儿子看養,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,也都 曉得些吟詩作對。雖然居住山庄,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,料想也配得過列位長老,若肯放開怀抱,長發留頭,与舍下做個家長,穿綾著錦,胜強如那瓦缽緇衣,雪 鞋云笠!”
Читать дальш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