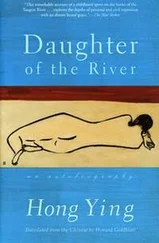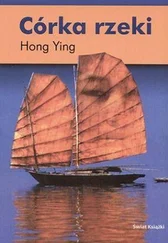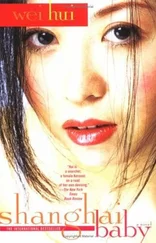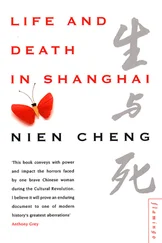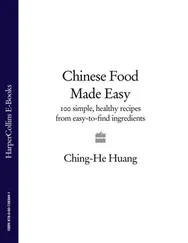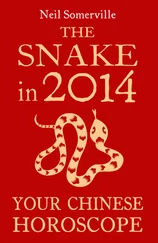“你让她顶一下我,我洗涮一下身上的血渍,就马上赶过来,总不至于血淋淋上台把观众吓死!”于堇耐心地向谭呐解释:“ 白 小姐对这个剧本熟透熟 透,对我的表演也完全领会。你让她穿上我的戏装,观众还不一定认得出来!”谭呐压住冒上来的火气,抬起头来看那个笑迷迷侧坐着装大明星的女人,恐怕于堇是 对的,这建议实际上是惟一可行的办法。
“ 白 小姐会同意吗?”谭呐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“一定会同意。”谭呐只好说:“莫之因也在这里,他会同意吗?”“莫之因不敢不同意!”于堇斩钉截铁地说。
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谭呐已经无话可说,于堇的话太奇怪。
放下电话,谭呐给自己的解释是:于堇因为丈夫死了,神志不清,才会想出让一个什么白云裳来顶替她。看来于堇跟所有的女演员一样,绝对无可理喻,这又不是小孩子玩家家酒。
但是若不开演,于堇不出场,事情会糟到不可收拾。有一个假于堇,哪怕蹩脚货,也比没有的好,观众会原谅她,才死了丈夫,演砸了,也都是可以原谅的。
谭呐这才转过身来,白云裳明白了一切似的,知道谭呐在看她,便打住与莫之因的话头,抬脸看着谭呐,朝他甜甜地一笑。的确,样子真的很像于堇。
这女人似乎听到了于堇在电话那头说什么。谭呐觉得他落进一个古怪的阴谋之中。
不过现在,无法之法也是一法了。他尽可能拖长他的沉默,最后不得不开口了:“ 白 小姐, 于堇 小姐想请你先顶一下她的戏,她正在赶过来。”白云裳站 起来,一干二脆地说:“行,这戏我熟,到中场休息, 于 小姐再上。”莫之因似笑非笑,他和白云裳是在进兰心大戏院门口遇见的,就一起上谭呐在剧场的办公室来 了。他不是聋子,当然听见谭呐和白云裳的对话。他猛地吸了一口古巴雪茄。谭呐看得明白,莫之因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安排,可是此人居然忍住未说任何话,谭呐 也就省了问他意见的麻烦。
只听白云裳站起来,对谭呐温柔地说:“ 谭 先生,你去照应整个班子吧,我知道于堇化妆室在哪里。”她翩翩然走出去的时候,加了一句,“十分钟后开幕。”
夏皮罗站在柜台左侧,注视着脸色苍白的于堇走出国际饭店大门。专门保护于堇的侍者脱掉制服,穿了一身西服跟着于堇出了门。夏皮罗朝电梯走去,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突然记起该是准备圣诞树的日子了,为什么不呢?
以往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为修殿节忙开了,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选礼物,精心准备做土豆煎饼和甜甜圈的材料,选最好土豆,最好的蜂蜜,烤香核桃块杏 仁片葡萄干桔皮苹果柠檬,用最好的肉桂粉和白兰地。父亲这段时间会带百年老店手工做的巧克力回家,酬劳母亲。他们家经营一家大食品厂。1938年春天,德 国吞并了奥地利,父母每日处于恐惧之中,商量去美国使馆申请全家移民。但是已经来不及了,那天奥地利的纳粹党徒破门而入,他们家被抢劫一空。
那天他在工厂里,还没有回家,邻居奔来告诉他,家里人已经被抓到达豪集中营去。看来有人借此报私仇:犹太人一个个都该倒霉,先轮到谁却没有道理可说。
他开始逃亡。
听说只要向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提出申请都可得到去上海的签证,犹太人必须持有签证有目的地,才可获准离开奥地利。
每天中国领事馆前都排有长龙,每个犹太人都想尽快得到这救命签证。但是他已在追捕之中,排队肯定被抓个准。他把自己的情况写好,护照装进信封, 当天夜里去了图书馆。在那儿,他找出一本中文书,从书上剪下了几个字贴在信封上,翌日上午急匆匆地到中国领事馆。他绕开门前排队的人,对站岗的卫兵说,这 是一封中国来的紧急挂号信,请马上转交总领事。卫兵不懂中文,信以为真,将信递了进去。
总领事果然派人把签证护照送到他信里说的地点。
他侥幸逃脱追捕,搭乘火车抵达意大利热那亚,转乘罗苏伯爵号邮轮到了上海。
在夏皮罗看来,上海有好多像狐狸一样不肯接受驯服的人。他也是一条狐狸,踏着自己的步子,走在这城市里。夏皮罗觉得他已经看到兰心大戏院那出话剧的演出,灯光暗下来,场子里鸦雀无声,安静地听得见个别观众的咳嗽声。
果然,幕升起的时候,暗黑的舞台上,是白云裳穿着露肩舞服的背影--那是于堇有名的背式出场。她的背后是两排唱诗班的孩子,稚气地嗓音唱着多声部的圣歌。
灯光渐亮渐收,照到女主角的背,她的腿伸出来一个微弓,一个长长的吟咏式的句子:“上海,你这建筑在地狱之上的天堂。”然后缓慢一个转身,眼神比身体先转向观众,像是一个远远的秋波。
台下轰然响起了掌声,上海老戏迷知道这是于堇的招牌姿势。亏得这白云裳学得微妙微肖。哪怕作为这戏的导演,谭呐以最专业的眼光,也只分辨得出两人嗓音稍有不同。白云裳略比于堇丰腴一点,化妆很巧妙,灯光之下,恍若一人。
白云裳果然对这出戏熟悉极了,让谭呐不由得怀疑起来:这个女人恐怕早就有上台的野心,不然今天怎么正好凑上了这机会。于堇说排练时白云裳都在场,他怎么没注意。这个白云裳不能轻看,就瞧她能把于堇那样骄傲的女人,弄得围着她转,就不简单。
谭呐本来怕她脱词,站在幕布边上,想在关键时提一把,但很快他就被白云裳的表演吸引住了。
女:我们会互相失去,失去到再也无法后悔,再也无法回到今天。
男:我们既然回不到今天,我们也只得相信这个命。(他站在窗前,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叠诗稿,在痛苦地撕。天不再深蓝,从未深蓝过。那么大海,我们走几步,就可靠近的大海,并未向我们展示过伟大的胸怀。
女:你是说,连这大海也不能容纳我和你,这坚实的土地,我一脚踏上去,也会踩空?(走向诗人,跪了下来,他不理她。如果,如果,我不能获得爱和平静,那我宁愿像一头暴烈的兽,撕碎这个罪恶之都。可是,亲爱的,你怎么办?
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了。白云裳演得相当熟练,从容自如。要是挑剔一点,那就是她台词记得太准,一字不易,反而缺少于堇特有的临场发挥的韵味。
谭呐朝助手挥挥手,让助手明白工作正常,及时催促一个个演员准时上台。
一直到第一幕落下,谭呐这真正松了一口气,他的发青的脸,渐渐恢复了人样的气色。他上厕所,对着墙,忍不住说:“真险,真险!”助手来找他,听见了,问,“谭导演,什么事真险?”谭呐笑笑,“天下本无事。”
于堇赶到兰心大戏院,直接到了后台,她从边幕看白云裳演出,如她预料的,这个女人演得很上心,很像那么一回事,连走路姿势也是一模一样。聪明人物,又用了心思学!看了三分钟,于堇就放心地到化妆室去了。
暗杀倪则仁的枪声,仿佛一声信号枪,这场角斗总算是正式开场了。
在香港,她依然在演戏演电影,但是别的演艺人士打麻将等片子档期的悠闲日子,她总是去休假,有时借口生病从剧组请长假。
Читать дальш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