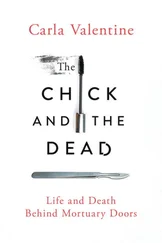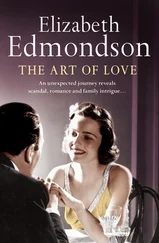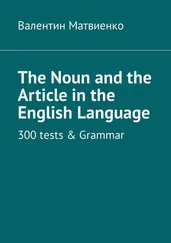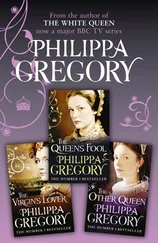“我觉得你在领导时髦新潮流,”他盯着她眼睛,“只要与众不同,就会吸引人。”
“你们西方人,猎奇而已。”她笑笑,就走开了,忽然她又停下。说,忘了,她和丈夫晚上请他去家里吃饭,就他们三人,便饭。
他看着闵的身影在树林中消失。以前开车、骑自行车都飞快,由着性子来。眼下校园里有什么事能快快地做,并带有刺激呢?
这个秋天,裘利安被他自己抛在中国这个最东边的临海之城,有着百湾之称的青岛。他背后是海湾,面前的山坡上一条大路,在树林中分岔出许多小道, 完全中国式的迷宫。他的表情并没有茫然,他的眼睛是镇定的。环绕着他的景物由浓变淡,只有他是明显的,西斜的阳光勾勒出他高高的身影,头发被阳光染得金 黄。
穿着湿衣服回家,两个仆人都来问裘利安,晚饭如何用?他没说话,不想马上回答这两个人。为什么要分派两个仆人?既然每个教授都是两个,至少两 个,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巫师嘴甜又快;田鼠不爱吭声,可能活是他做得多,这两人住楼下一间。他们不是看不出这个洋鬼子不喜欢他们,他在家时他们尽量在厨 房,或自己房间,或干脆出去买东西,不在他眼前晃。全世界仆人都一样,主人不想看见你时,就得躲开点。
你们吃自己的。裘利安说,他有饭局。
太阳已经沉到山峦后,但余光还在海面,艳丽地染了海水。到 郑 教授的房子,走大路要近一刻钟。而另一条下坡的小径,林荫覆盖,地面是多年积聚的落叶,滑溜溜的,很少有人走似的。这条陡路,慢慢走,只要十分钟路,这样一来,他们几乎可以说是邻居。
裘利安敲响门,没人应,他就绕着花园走。系主任的房子和他的几乎一样,但花园大得多,修剪整齐,没有篱笆,花园大小是房主自定的。园里正是花季,香味芬芳浓郁,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,一抬头,闵和郑正在他面前,微笑着。
裘利安没穿西装,只是换了件衬衣。衬衣领口还敞开两颗扣子,头发又长了些,卷曲着没有挂下来,只是显得蓬乱。
闵说,只有你一人从我家花园进来,像强盗。
裘利安举双手投降,请原谅我什么礼物也没带。
郑爽快地说,来我这儿就像到自己家一样,朋友们都这样。
他们的家里有许多古董古陶器,连椅子也是几百年的历史,玲珑的雕花雕兽,扶手已经摸得光滑。“也算传家宝吧,结婚时,母亲给的。”闵领着裘利安 参观房子。卧室的屏风门帘灯罩都是日本式的。闵的书房很大,有一张大书桌,一个单人榻榻米在她的房间。看见裘利安注意,闵就说他俩都在日本呆过好一阵,闵 少女时代还在那儿读日本文学,比郑更喜欢日本。她是夜神仙,喜欢工作到天亮,中午补个小觉。工作晚了,怕影响郑休息,就在自己书房睡。
她和丈夫分开睡!裘利安心一动。
闵陪着裘利安下楼。裘利安觉得自己有点好笑,总不免往男女之事上想,他脸上又露出自嘲的微笑。闵完全没有化妆打扮,没有涂口红。的确如她所言,便饭。闵说,看来得改休息和工作时间了,想辞去《青岛文学》杂志的编辑工作,现在事多。大约是指上他的课,他猜。
闵注意到他在沉思:“怎么啦?”
“你在做的事太多,我在做的事太少。”他说。
闵看看他。
裘利安想只有他明白自己在说什么。
房子非常整齐,是有个主妇的家庭。该有画的地方就有画,该空的地方就空,不像母亲家里混乱得有趣。但裘利安喜欢她家客厅一幅极大的挂毯,笙歌夜 饮,古装男女,不会等到明早。他喜欢挂毯上面那种泛黄的调子,暗暗沁出欢乐的暖色。壁炉上有个镜框,里面是一张剪报。裘利安走近一看,《北平晨报》 一九二四年的,十多年前的中文报纸,上面有照片:闵,郑和另外十来个人,还有一个大胡子的印度人。“泰戈尔?”他问。
“是他,”郑说,“我们的媒人。”
原来这位首先在伦敦成名的孟加拉诗人,在中国受到最大欢迎。《吉檀迦利》是中国人最着迷的,这个惟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,是新月社集体的崇拜对象,郑解释说。
东方人还是喜欢东方人,裘利安读过泰戈尔的诗,感到他缺少智性的张力。叶芝和庞德对他的推崇,有点奖掖的意味。闵看着柜子上的留声机唱片,沉吟一下,对裘利安说,你喜欢听音乐,晚上走时你拿去听。音乐能帮助你理解这个文化。
他的确只带足了书。闵专心挑唱片,说大都是她和丈夫在欧洲度蜜月时买回来的。柴可夫斯基,莫扎特,肖邦。裘利安看到唱片上的中国字,就问郑:中国音乐吗?能不能借这些?
郑说,女主人说拿就拿,不是借。
裘利安连连说,太好了太好了。
郑被他高兴的样子感染,对闵说汉语:“裘利安怎么像小孩?”
“他不就是小孩的年龄!”闵说。
他们的中文说得较快,裘利安只抓住他自己的名字和“小孩”两字,忙问两人在说什么?他们却相视而笑,裘利安也笑起来。郑说,闵写诗喜欢清静,以前,也就是十多年前,在北京时,新月社人来人往,她都嫌不够热闹,还要放音乐,现在变了。
裘利安觉得郑和闵两人都没有把他当外人,他们和其他中国人不太一样,很真实。他也觉察到自己的真实,从到青岛时就有的一种莫名的虚幻感,这时竟没了。
闵找来徐的诗集给裘利安。徐,他记起了,新月社中心人物,中国文人总在谈此人的名字。诗集扉页有徐的照片,戴个眼镜,对一个男人来说, 长相太 清秀,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。他翻着诗集,排成竖行的中文,每一行诗长度都一样,很整齐。中文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,那不就是法文诗那种音节体吗?但是, 郑坚持说中国现代诗与英语诗一样,有音步。他对闵说,你念念,你是京调儿。
闵说每个中国学生都能背徐的一些诗,尤其是《再别康桥》一诗,人人皆知。如果说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,这便是一例。
轻轻的我走了,
正如我轻轻的来;
我轻轻的招手,
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那河畔的金柳,
是夕阳中的新娘;
波光里的艳影,
在我心头荡漾。
闵继续读下去,诗共七节,第七节呼应第一节。
悄悄的我走了,
正如我悄悄的来;
我挥一挥衣袖,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裘利安没打断闵,实在的她说中文时声音太好听,的确是有节奏的音乐。他说:“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首说我母校的诗?”
闵说有现成的好译文,而且她能背。最后一个韵词结束,裘利安再也按捺不住,想大笑出声。不笑,他觉得自己会憋死。什么三等雪莱的货色?他忍的时间太长,脸有点涨红,闵和郑似乎没有注意到,他马上装做是喝酒呛着了,冲到花园门口咳嗽。算是遮掩了过去。
闵和郑没有再读诗,他们在讲徐一九二三年在伦敦的事,讲得津津有味。
他们说连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亚瑟·韦利也向当时做留学生的徐请教。裘利安知道这人,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,就住在戈登广场三十六号,他每天骑 自行车去上班,路上常碰到。因为倾慕布鲁姆斯勃里圈子,而中国诗是当时英美文坛的时髦题目,所以后来也被邀请来参加聚会,但母亲他们认为他太没劲,就没太 邀请他。但裘利安不想说韦利这老实人的坏话。
Читать дальше